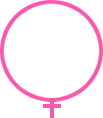深圳女孩逛街遭强制传唤 警察执法需规范

有微博爆料,近日在深圳宝安西乡流塘大门口,两名女孩逛街,被警察检查身份证,后被强制传唤。而涉事警察与女孩对话视频也在网上热传,视频中该警察粗鲁言语、恐吓言论频出。此后深圳宝安警方回应中将事件定性为“民警执法不规范”。据最新消息,当事民警被停止执行职务,等候进一步处理;宝安公安分局局长周兆翔对两名当事人赔礼道歉。

当事民警存在过错已无疑义,争论只在于性质是执法不规范还是违法。当事民警已被停职,宝安公安分局局长也已向两位当事人和社会道歉。但就在公众热议警察执法乱象的时候,微博上个别认证的警察个人账号发表惊人之论,说“警察依法盘查你怎么了?你以为你是谁?”,进一步激化了警民冲突。
警民矛盾激化对整个社会来讲只能是双输的结果。
一个安定繁荣的社会,离不开民众对警察权威的认可和维护。但个别警察以为执法可以有瑕疵,但民众必须无条件服从,则是对法治的误读。
法治社会有两句准则:“法无禁止皆可为”,“法无授权不可为”。前一句是对公民说的,只要法律不禁止,公民就有行为自由。比如法律并没有规定逛街必须带身份证,所以这次事件中的两位女生并无过错。后一句是对公权力和执法者说的,任何一位执法者都必须在法律授权的范围内行事。比如法律授权警察查验公民身份证但同时要求必须符合特定条件,所以警察不能随心所欲地查验身份证。
执法者切不可把自己等同于法律,把所有公民等同于犯罪嫌疑人。然而现实中,个别警察习惯了家长作风,如本应该主动出示证件,但有些警察非但不主动出示,遇到对方要求出示证件,反而认为对方刁难自己,因而产生敌意。
深圳这位警察之所以引起公愤,是因为其粗鲁言语在执法者身份陪衬下备显错位。个别警察认为公众小题大做,是因他们已经习惯了粗糙的执法方式。陈某在事后还解释说,自己是把两个女孩当孩子对待,“老百姓误解我在耍权威,但我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耍权威。”即使我们相信他会以如此过分的方式来教育孩子,一位警察也没有权力把公民当孩子来恐吓训斥,他必须严格遵守法定的流程和方式。
有的警察一被质疑就会说“我不是在服务,我是在执法”。但执法者并不比其他公民高一等,执法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,而不是侵犯公民权利。还有警察习惯于抱怨“工作又苦又累还没人理解”,首先要承认警力不足这一客观情况,但试图以粗暴执法赢得公众的理解可谓缘木求鱼。
警察规范执法是双赢,警队内部同样受益匪浅
如果一个社会,警察执法总体来看是规范化的,对民众而言,好处自不待言:由于警方的行为,始终处在预期内,警权可受到限制,民众可免于恐惧。
但这只是好处的一面。另一面,对警队自身,规范化执法同样利大于弊。就以这次“警察盘问两女孩”事件为例,最终落得一个当事警察停职、局长道歉的局面,起因仅仅是因为执法过程中很寻常的身份核验问题。
关于警方执法时,要不要出示警官证,可不可以查你身份证,这其实是一个很老旧的话题。可直到今天,仍有很多人,甚至很多专业人士认为,“穿着制式警服不用出示警官证”。比如微博上一个检察官认为,着装即代表赋权,如果纠缠于此,警察自然会认为你在挑衅。
这一问题,没有争议。具体的法律条款这里就不列了,明确告诉大家几个结论:1、公民没有随身携带身份证的义务;2、警方查验公民身份证,需要有特殊的情境。在街上逛街的两个女孩,不属于这些情况中的任何一种;3、警方除了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,或处置重大、紧急警情这种情况,都应主动出示证件。
有人说,不要装,穿着制服的警察出示了证件,你就能看出来是真的还是假的?这里面存在的误区,正是规范化执法的意义:警方主动出示证件,体现的是程序价值,而非实体价值,是表现一种双方均存在制衡对方的权力。
为什么公安部三番五次地强调一定要规范化执法?因为公安部也想保护自己的警察。规范化执法对警队最大的好处是,只要你按照规范来,就可以免责。在某些事件中,本身不存在任何利益问题,规范化执法,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另外,长期不规范执法,会使得一些警察动作变形严重,其行为甚至超过“不规范”之范畴,有涉嫌违法犯罪之风险。
可以发现,最近这几年,每当警民对立事件发生后,警队内部怨言载道,直言警察不好做。这些不满,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。第一,抱怨警员不足,工作压力太大;第二,感慨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威。
上述第二点,很难得到警队之外群体的认同,甚至可以说背后有极大的认知撕裂。警察如果缺少执法权威,首先是因为执法公信力的丧失。像不佩戴执法记录仪、随意搜查盘问、暴力逼供、超期羁押等不规范执法行为,都在一次次重创公信力。而规范化执法,是执法公信力重建之根本。

国内警察常常羡慕美国警察的威权,尤其是“敢于开枪”。且不说这根本不是事实,即便是事实,也建立在美国民间有几亿把枪支,两国警察执法时面对的威胁不可同日而语的基础上。况且,美国警察执法过程中有非常细致的执法规范和标准规程。举一个例子,美国警察拦截检查车辆时,应将拦截地点和被拦截车辆的车型、颜色和牌照号码告知指挥中心(登记备案制度),如果拦截发生在夜晚,警察必须使用交通警示灯和探照灯,并且探照灯应当对准嫌疑车辆的后视镜。
社会在变,警察的管理职能也应跟着变
社会在变,警察自己的业务范围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。19世纪,美国大城市迅速发展,由此带来了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,移民使得城市人口空前膨胀,工业化又加大了贫富差距,因此才诞生了美国的现代警察制度。在彼时,警察的职能,最主要的就是维护治安,增加公众安全感。
但是,在1976年至1978年间,美国警察服务研究课题组(Police Service Study)在纽约州60个社区进行了调研,想看看平日里警察都在干什么。研究显示,警察的大部分时间是向公众提供服务。在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首要工作时,执法手段侧重于“有效”;在服务民众变成警察的首要工作后,执法手段自然应该转变成“亲民”。
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。社会治安状况普遍不好时,在1983年至1987年间开展的严重践踏法治的“严打”,在当时都可被接受,这可就不是“执法不规范”的问题了,公安、检察、法院三家公然合体,“可抓可不抓的,坚决抓;可判可不判的,坚决判;可杀可不杀的,坚决杀。”
1980年,公安部在杭州开了一个会,定调刑侦与基层工作分开,破案工作归刑侦部门,基础工作归派出所。这就意味着,作为国家暴力的末梢,基层派出所主要是作为国家权力与社区对接的组织,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服务社区居民。但由于“严打”来临,这一方针发生根本逆转,基层派出所也完全参与到“打击犯罪”中。
“严打”这种所谓“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”,让基层派出所也广泛参与到“打击犯罪”中去,模糊了定位
这一政策的贻害,正在逐渐显露出来。派出所多和社区居民接触,而社区居民绝大多数都不是违法犯罪嫌疑人,但警察的执法态度,已经很难再扭转。虽然在04年,公安部再一次提出,中国治安政策要从“国家中心”向“社区中心”转变,“民警应通过各种途径多参与社区事务”。但结果是,对于服务居民的日常性工作(如自行车、手机被偷),警队的兴趣并不大;在日常执法活动中,也更愿意彰显自己是“暴力机器”这一面。
所以,尽早规范化执法,打造“服务型警察”,对公众对警队来说都是一件好事。因为原本舒适的环境,正在变得越来越不舒适。同时,在各类公职中,警察是与公众接触最密切、最能让公众感受法治进程的职业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警方的执法方式转变迫在眉睫,这是外部环境在逼着进步。
责任编辑:胡玲玲



- 关键词
- 警察
- 警察执法
相关阅读

- 评论